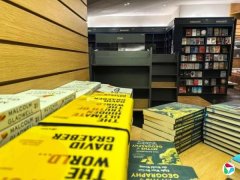岁月是把杀猪刀,大家也许已不再年少,但只要健康允许,生活依然可以有激情。有激情和追求,就多少会有志同道合者、有门路。这之中,有钱没钱甚至不是重点。
前个星期六,国内外大新闻不少,但有一则小的特别好玩,也特别让我上心,就是一群公教附小的老同学,50来个相约好穿上校服,回到滑铁卢街的旧校址,来个很特殊的新春同学会。他们上小一那年,正好国家独立,但这是他们独有的SG60,相知相识60年,真的不简单啊。
其实近几年,他们都有办聚会,要不就是一起旅行,还细分了几个不同的兴趣群组,情谊一直都在。一个说,总有人会离世,因此特别珍惜每一次的相聚。
有好几个老师也被请来了。大家唱校歌,翻看泛黄老照片,当然也有聊不完的当年——毕竟在这里以及隔邻奎因街校舍,一起念了六年10年甚至12年的“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,阿门”,估计还有谁谁谁被老师藤条伺候,以及那些个追附近圣尼格拉女生的成功和失败故事……
我请主任告诉前线记者,让“同学们”多谈一些,文内尽量直接引述。其实担心的,是女记者太年轻,无法体会和写出人家的情怀。还好稿子交上后,水平超预期,我认识的不同年龄段的公教人都很认可。年轻编辑也压力山大,构思了一晚,最后生出两个都不错的标题版本,于是网上和报纸分开用,隔天一位岁数更大的校友在群里写道:不忘“同窗旧梦”是神笔!
再穿一回小学校服,你敢吗?
以上这则新闻我之所以多写几笔,因它至少有两个难能可贵。一是试问有多少人,到“六老七十”了,还能把四五十个小学同学都约出来?能联系上五个10个的已相当厉害,更多不都是人生路上走着走着,也就散了。另一个是未泯的童心。换作是你,再穿一回小学校服之前,是否得先想个三天三夜?也许同学会的邀约,还不一定答应出席呢。
总之对比现实,他们的“返老还童”是个特例。而现实是什么呢?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开始出现暮气。从周遭的身影、眼神和人际的互动,总能察觉到孤独、百无聊赖、没有存在感、生活失去意义甚至受抑郁症所困扰的长者越来越多。
我曾经以为,上几代的老人会比较辛苦,因为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,他们是顶端的少数,有同样处境,能同病相怜的人相对少,被边缘化的情况会更严重;而现在,是婴儿潮的一代大家一起变老,并且教育和见识水平都要比以前的人高,照讲应该更自信、更快乐一些才对。可惜,趋势并非如此。
比如孤独死,在家庭人口偏多的年代,几乎闻所未闻,如今却经常能在报纸上读到。
数字也告诉我们,老人自杀的个案很多,只是媒体基于社会责任,一般都不处理,偶尔见报的,肯定是冰山一角。
又比如垃圾屋的问题,主要是因为火灾,或者不幸死了人才见报。根据观察,有在家中囤积废弃物习性的,以老人居多,并且也是一种心理疾病,是需要被关怀,被治疗的。
一个星期前的傍晚,在家附近的公园,一个被女佣搀扶着的老者主动跟我聊天,说是过来看孩子的,并说他已90岁了,是印尼商人,到处做生意,附近还有自己的公司。当时谈最多的,是他在中国福州的投资,还提到自己祖上是满州贵族还是皇族什么的,我姑且听之。以他的年纪,精气神还算不错,但看得出很寂寞,很珍惜我这个能够交流,起码会礼貌点头的听众,要不是女佣察觉天色已晚硬把他拉走,他应该还有很多人生的阅历要跟我分享。
导致老人不快乐的原因复杂,其中一个,是现代社会结构原子化,亲情变淡薄了。
孤独终老不是宿命?
好几年前,同事在星期天写过一篇专题,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当时下的大题是“孤独终老不是宿命”,封面索引打了“你可以选择,不在孤独中老去”,都是满满的正能量,但内容所反映的实情,以及视频的个案却让人心情沉重。报道引用了一个调查,说华族老人所获得的陪伴和情感支持,是各族群当中最少的。
必须说很多的疏离,与孝不孝顺无关,而是实际的困难,例如因为少子化,抚养比本来就偏低,加上很多子女本身也是有工作有小孩,自顾不暇的双薪家庭,能分配给老父母的时间本来就不多。再有就是环球化的冲击。我旧家隔壁的老妇,10多年来就只有女佣相伴,据她说,几个孩子都移民美国、英国和澳大利亚了。随着教育水平持续提高,跨国婚姻日益普遍,类似的代际离散情况估计还会增多。
第二是科技进步太快,例如数码化已深度嵌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跟不上的老人很多。一些则是英文不好,和社会有了隔膜,感觉一切都变得陌生,还处处碰壁。稍年轻一些,还留在职场的,一边得拼命追赶,一边还可能遭遇歧视……
再有就是贫困。毕竟社会上还有一大群人,在他们壮年、生产力处于巅峰时,国家还没完全发展,自身所受教育也不多,因此尽管勤奋一生,收入和积蓄仍然有限。据新加坡管理大学幸福老龄化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项研究,有32%之多的57岁至76岁受访者担心,自己买不起必需品或支付不了账单。而这些还仅仅是“担心”,那些掉入更底层的,生活需要接济,就更难和快乐沾边了。国家当然会给予关爱,在星期二的预算案声明中,给年长者的援助就有好几项,但摊到每个人身上,都只能是小补,起不了“质变”的作用。
最后,最可怕的无疑是疾病,让它找上,长痛短痛都是痛,也都是折磨,除非内心无比强大。有人可以安贫乐道,但你肯定没听说过有安“病”乐道的。
健康与财富+亲情与友情+学识与智慧……这些专家总会开出的“乐龄”方程式都没错,问题是:要把财富和所有的“XX自由”都凑齐,就如同中大彩,概率太低了。
Just do it,别再等待和蹉跎了
怎么办呢?除了遭遇贫病,我想有很多的快乐与不快乐,还是存乎一心,操之在我的,意即可以借助内心的调适,在心态上、观念上尝试做出改变,好让快乐多一些,而过程中,根本无须太在意社会眼光。也许上述那批老公教,早已踏出这一步,实践着“我的快乐我做主”的生命态度。把小学校服穿在身上,图个乐趣谁说不可以呢?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:只要我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!
在大合照中,有一个我常以“星爷”喊他的朋友,很可以做为代表人物。我们很熟,但约他不容易,因为他总是在异乡的旅游路上,然后时不时在群组里,晒出在各个景点打卡的照片。我最佩服的,还不是他徐霞客般的兴致,或不断进步的摄影技术,而是他总会从地面跳上来,让自己在空中定格。我们都曾在一个篮球队里,跳都不是问题,但要我在人群中和镜头前如此自嗨,我肯定放不下矜持,所以常以捉弄但又带鼓励的口吻,要他多跳多拍,好让大家也跟着开心。这不,几天前刚准备写这篇专栏时,他又给群组发照片,背景是老挝万象的凯旋门。我回了一句“滞空能力不减当年……”他跟着发来在万荣的乡间,从五六米高台跳入潟湖中的视频。
运动品牌耐克的“Just do it”标语,其实很好地概括了这种信念。做就是了!别太拘泥于世俗眼光或人言人语。有人可能说,标语针对的是年轻人,有挥霍的本钱,输得起;但换个思路,年纪大了,不是更应该只争朝夕,不好等待和蹉跎吗?
找到喜欢干的事,就放胆去做吧,千万别自我设限,这包括尝试新的运动,或投入到某个艺术领域。我有一个七零后的女性友人,最近撸起袖子、拿起刷子,很认真在跟一位大师学抽象油画。且不管能否大器晚成,这种自发性,就很值得按赞。还有就是可不可以在社区、宗教或者理念倡导中,寻找有意义的参与,既能帮到他人又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;或想到有什么远方,很想去玩去看看的,就赶紧策划吧。一句话,别犹豫和畏惧,Just do it,你又能输掉什么?
西方人,更懂得活出自我
相比之下,西方人一般比我们东方人,更懂得活出自我。有一个苏格兰朋友曾跟我说,他老妈80多岁了,还在打高尔夫球,虽然以前可以360度挥杆,现在双手不能拉到背后,少了90度,力量也大不如前,但还是自得其乐。在我们这里,你可曾见过,七八十岁华人老太太上球场的?
我也总是在想,我们东方人,是不是为子女操太多心了?但子女总会离巢高飞,有他们的世界。也许应该也学学西方人,多为自己而活,不会把一生牵绊,都放在下一代的身上?
还有如果老伴不在了,是不是应该再找对象,再谈个恋爱?如果两个人觉得投缘、感到舒服,可不可以不要婚姻枷锁,但一起过日子,好相互照顾?你可能不同意,但我觉得东方的老人,有太多各种传统束缚,挣脱不出来,要快乐就比较难。
岁月是把杀猪刀,大家也许已不再年少,但只要健康允许,生活依然可以有激情。有激情和追求,就多少会有志同道合者、有门路。这之中,有钱没钱甚至不是重点。有钱当然选择多一些,但没钱也能有没钱的快乐时光。我经常在邻里咖啡店里,看到上了年纪的男人们,三五成群几杯酒下肚后,就这么天南地北聊一整晚,顺便和啤酒西施们开开玩笑,相互逗乐。不正经吗?我不这么认为,至少好过一个人成天足不出户,结果把病都给闷出来。
总之,已一脚踏入迟暮的男儿和女儿们,都应当自强,而自强的关键是随心所欲,做自己的主人,不要让别人和世俗的眼光把你困住。这也是“穿回小学校服”的公教老男人们,给我的最大启发。
所以,如果再有同学会,可要记得报名哦!
也不妨给自己弄个学习清单,例如看看“技能创前程”补贴了什么课,当然别因为不用自己的钱就三分钟热度。
我呢,就试着下次拍照时,学一下“星爷”,敢敢跳起来,做个开心人!
(作者是《联合早报》副总编辑)